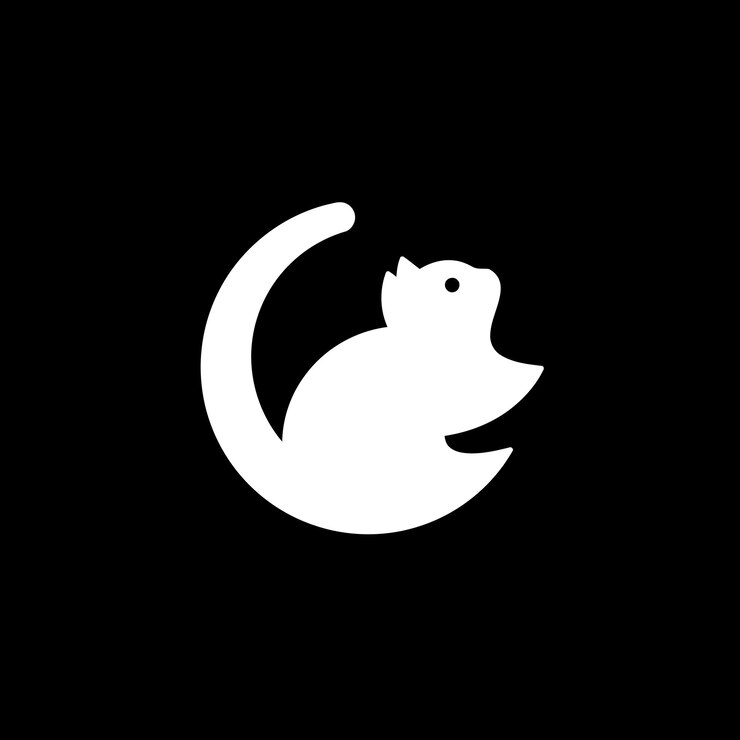苏轼一生坎坷,却极幸福。
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,儿子也从没让他失望过,遇见的每一个女人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。
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,一生逍遥烂漫,任他南北西东。
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着无数朋友,可真正贯穿一生,永远让他可以托付后背的只有一位。
苏辙。
…
苏辙比苏轼小两岁,‘轼’的意思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,‘辙’则是车后的痕迹。
如名字那样,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。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,兄弟二人形影不离。
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,各自娶妻后父子三人同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。
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中,兄弟二人同时金榜提名,名动京华。
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时,家乡传来母亲病逝的消息,父子三人返乡守孝。
…
古代官员们大多都讨厌守孝。这会动摇他们的朝中根基,进而耽误前程。所以在父母去世时他们有的甚至都会隐瞒不报。
可苏家兄弟却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,他们都明白这是他们最后的相处时光了。
一日夜雨,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“宁知风雨夜,复此对床眠”。
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,守孝期满制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,再难相聚。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一起回到家乡,还能如今晚一样夜雨对床,种豆南山。
自此,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。而这一守,便是四十三年。
…
公元1061年,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,考官欧阳修感叹道:“苏氏昆仲,连名并中,自前未有,盛事!盛事!”
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,苏辙则放弃去商州任职,在开封陪伴重病的父亲。
哥哥要出发了,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二十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,他们相约十天诗成便鸿雁传书。
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。
天色将暮,兄弟拜别,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,帽带在凛冽的西风中飘扬。
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:“亦知人生要有别,但恐岁月去飘忽。寒灯相对记畴昔,夜雨何时听萧瑟。”
…
此后多年,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。
公元1069年,因为苏轼不认同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,苏氏兄弟遭到排挤。苏辙先请外放,一年后苏轼也接到杭州通判的任命。
赴任途中,苏轼到陈州去看望苏辙,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。
分别时苏轼在《颍州初别子由二首》中写道:“近别不改容,远别涕沾胸。咫尺不相见,实与千里同。”
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,却始终适应不了分别。
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,高度契合的思想,相似的政治理念,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中越发成为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。
苏轼说“嗟余寡兄弟,四海一子由”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庆幸我有弟弟啊。
苏辙回复:“手足之爱,平生一人。”哥哥你何尝不是我的唯一?
有人说苏辙刻板,文章悟性不如哥哥。苏轼马上说:“我少知子由,天资和且清。岂独为吾弟,更是贤友生。”
苏辙说自己没有哥哥聪明,“幼学于兄,师友实兼。志气虽同,以不逮惭”。
苏轼说:“子由之文实胜仆,而世俗不知,乃以为不如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,其文如其为人,故汪洋澹泊,有一唱三叹之声,而其秀杰之气,终不可没。”
都说苏辙一生都在捞哥哥,殊不知苏轼的真诚热烈同样感染了苏辙一生。
…
公元1076年,苏轼到密州任知州。
他着手城市建设,以工代赈,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荒废楼台修葺一新。
他写信问弟弟要亭子名字,苏辙取老子《道德经》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文意,赋名“超然台”。
苏轼大喜,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。
‘春未老,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看,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寒食后,酒醒却咨嗟。休对故人思故国,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’
中秋之夜,苏轼独饮大醉后思念弟弟,写下那篇著名的水调歌头。
‘我这样一个豁达之人岂能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?但是为了你我偏要做‘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’的痴人’。
最深沉的爱大抵便是如此。
…
公元1079年,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。
乌台诗案爆发了。
这个大文豪被拷打羞辱,至于关在隔壁牢房的大臣都感叹道:‘遥怜北户吴兴守,诟辱通宵不忍闻’。
万念俱灰下苏轼给弟弟写下绝命诗:“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人间未了因。”
生命的末尾,他还念着当年的约定。
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宋神宗,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。
经过多方营救,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,苏辙也因故被贬筠州。
历经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,万千悲苦涌上心头,给弟弟写下了那首西江月。
‘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?夜来风叶已鸣廊,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贱常愁客少,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,把盏凄然北望’。
人生造化,不外如是。
…
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,他们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都托付给了弟弟苏辙。
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,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。
他们到达的那一天,苏轼专门起了一个大早,赶到二十多里外去迎接他们。
历尽劫波兄弟在,之前尽写些诸如‘寂寞沙洲冷’等诗的苏轼心情也好了起来,写下:‘余生复何幸,乐事有今日’。
此后苏轼逐渐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,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。
他在新成的雪堂写《初秋寄子由》说,“百川日夜逝,物我相随去。惟有宿昔心,依然守故处。忆在怀远驿,闭门秋暑中”
对于哥哥的涅槃,苏辙感到由衷欣慰。
…
神宗去世后,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。
苏轼也在一年时间里从一个八品闲官起复成了三品大员。
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,回到朝廷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。
正如他自嘲的那句话:‘一肚子的不合时宜’。
他再三请求外任,除了对时政心灰意冷外,也是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。
苏轼外放的第二年,苏辙任中大夫、守尚书右丞,行宰相事。
可好景不长,公元1094年,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。
短短半年内四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,状况比当年黄州更为不堪。
三年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次被贬儋州,苏辙被贬雷州。
…
渡海前,兄弟见了人生当中最后一面。
他们对坐饮酒,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。
眉山老宅当年手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?
那年在唤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?
嫂子墓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已经漫山遍野了吧。
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个中年人了吧。
我们来世…还能做兄弟吗?
三年后,苏轼病逝,临死前谓左右曰:‘惟吾子由,不及一面而诀,此痛难堪’。
苏轼死后苏辙便将哥哥家人接到自己家来住,倾心抚养,视若己出。
…
很多年后,苏轼在海南培养的第一个举人姜唐佐来看望苏辙。
东坡遇赦离琼时,赠唐佐一句诗:“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”。并对他说:“异日登科,当为子成此篇”。
此时残篇尤在,斯人已逝。
苏辙擦去泪水,为哥哥补上了后面两句:锦衣今日千人看,始信东坡眼力长”。
…
苏轼去世十年后,苏辙也走到了人生尽头。
位极人臣的他并未另择风水宝地,而是选择埋在了哥哥身边。
夜雨之约,至此了结。